2017-07-24 来源:凤凰文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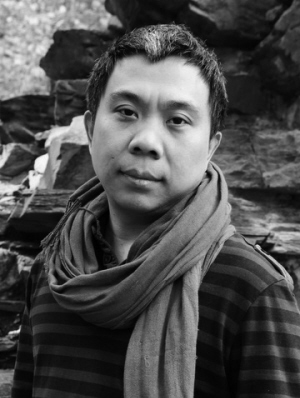
赵野(来源:凤凰文化)
文|赵野
1
去岁六一,在“风啊水啊一座桥”的木心美术馆,我第一次见到张奕明。主持人潇男介绍说,他是留美的钢琴博士,此次公和年会庆典的特邀演出嘉宾。一般印象里,演奏家不管几流,都有一种特别的范儿,总是被架在空中。奕明却很朴实,衣着随意,目光清澈,一头蓬松的卷发,很接地气。那天他弹的是葛甘孺的《古乐》,非常现代的钢琴曲,各种不谐和音像是被砸出来,不时还要用手直接去拨钢琴的琴弦。在座诸公,虽都为各方面的豪杰,独对现代音乐少有濡染,应该是基本不懂。这个作曲家的名字,也无人知道。但奕明自有强大的气场,让人感觉天才了得,把大家都征服了。演奏结束,掌声雷动。
接下来的交流中,奕明说他在梳理理民国以来的中国钢琴音乐,他认为很了不起,是一座宝矿,可惜无人问津,已近废弃了。然后提到了汪立三,说刚在NAXOS公司录制了三张CD的汪立三钢琴音乐全集。这也是中国音乐家的钢琴作品全集,第一次在国际上录制发行。
我平日自诩热爱音乐,却第一次听到葛甘孺和汪立三的名字。以前我以为中国的现代主义音乐,是从郭文景瞿小松那一拨开始的。尚记得约三十年前,在四川外语学院一个朋友的宿舍里,郭文景带来一盘磁带,是他刚完成的《蜀道难》,我们听了一个晚上,大呼过瘾。去年在国家大剧院听了《蜀道难》的现场,仍是感觉才华横溢,光芒四射。加之以前听过郭的《夜宴》的现场,我的谱系里,中国当代音乐,就等同于郭文景和他的同学们了。
今年的公和年会,奕明仍是演出嘉宾。这次他带来了江文也,我们遂有了共同的话题。几年前我就发现了江文也,认为他是民国时期最杰出的音乐家。江文也出生台湾,十二岁去日本受教育,二十余岁即在国际上屡获作曲大奖。1936年他初到北平,即被强大的文化传统倾倒,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及民间音乐,探索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,创作中国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。他在孔庙音乐里,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境界,没有欢乐,没有悲伤,像空气一样,无所在,也无所不在,他称之为“法悦境”。江文也深信这是东方文化最珍贵的宝库,独具世界上其他类型音乐没有的特殊性。基于这种信念,他在1939年,完成了堪称伟大的《孔庙大晟乐章》。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乐,同时具有古典神韵和前卫精神,“是一项文化想象的重塑,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(王德威)。”他继而深入孔子仁学,写作了《孔子的乐论》一书,检讨仁和乐的关系。最近几年,我一直在思量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,江文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个案。
因为奕明演奏江文也,我在朗诵诗歌时,特地选了《雁荡山忆胡兰成》这首。江文也与胡兰成,应该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,一时也捋不清楚。晚宴奕明和我正好一桌,我们喝着海涛兄提供的上好茅台畅谈。他说下一张唱片,就要全部弹江文也的钢琴作品,我说我也一直想写一首有关江文也的诗歌。他说他写了一部《汪立三评传》即将出版,我遂讨要电子版先睹为快。他说要么你就为此书写个序吧,我就借着酒劲应承下来。
是为缘起。

张奕明(来源:凤凰文化)
2
汪立三1933年生于武汉,祖籍四川乐山,祖父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人,父亲则有狂士的禀赋性情,并遗传到他身上。1937年汪家迁居成都,差不多半个世纪后,我也来到了这个城市。成都有一种迷人的精神气质,让人松弛,我完全熟悉它的慵懒和颓废。
那样一个时代,在成都长大,对汪是一件幸事。一开始他喜欢文学和绘画,这两种癖好其实随了他一生。抗战胜利,大哥带着两箱唱片回家,这份特别的滋养改变了他的命运,他进入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学音乐。1950年汪出川,先去天津,随后辗转上海,以钢琴和作曲两个第一名,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,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。
卓越的音乐天赋,以及从父亲那儿承继下来的狂士风范,让汪很快就成为学生中的风云人物。在以一首钢琴曲《兰花花》瞬间成名后,汪和同学蒋祖馨、刘施任在《人民音乐》杂志上,发表了一篇长文,质疑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交响乐技术不过关,功夫差,并用了“刺耳的音响”、“一片混乱”、“最难听的”、“单调啰嗦”、“令人感到烦躁”、“离奇古怪”等字眼。结果是路人皆知,一阵急风骤雨般的狂批后,汪和他的同学被打成右派,先是下放浦东劳动,随后北大荒用猪肉或木材,与上海作物置换,把这批有专业技能的人要了过去。汪被分配至合江农垦局文工团,以佳木斯为中心,那是一个“比萧红的呼兰河更北更北的地方”(汪立三),一直到1963年,上调哈尔滨艺术学院,后并入哈尔滨师范学院。三年后,文革开始了,汪和其他老老师一样受批判,进牛棚,下农村,再回学校。从被打成右派,到文革结束,约二十年间,汪的生活本身,似乎没有太多可以特别说的。那个时代,有太多悲催的人与事,他不比别人更幸运,也不比别人更不幸,当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作。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,他这样的人,心里可以装着一坐火山,时代的、个人的乃至身边的一切伤痛和劫难,都可以先慢慢融化,等着命定的爆发。1979年彻底平反后,汪迎来一个创作的井喷,接连完成了四部重要的钢琴独奏作品:《东山魁夷画意》(1979),《他山集》(1980),《幻想曲两首——李李贺诗意》(1980前后),《二人转的回忆》(1981)。奕明写道:“这几部作品显示了某种空前绝后的特征:那是中年的成熟度和饱满度,以及多年不能写作而憋出来‘井喷’式气质。”我记得在诗歌界,大概是在九十年代,也有人提出“中年写作”的概念。
哈尔滨师范学院,1980年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。我大理理的邻居、诗人潘洗尘1982年考入哈师大中文系,当我向他谈起汪立三时,他说他们认识,但没有多的交集。洗尘当年应该听过《东山魁夷画意》这个曲子,他说他就是从那儿,知道了东山魁夷这个名字。汪随后出任了哈师大艺术学院院长,陷入琐碎事务中,又是多年没
有像样的创作。北大荒及哈尔滨的生活,汪自比为苏武牧羊,还多了二十多年。据奕明的研究,汪的创作正好集中在三个时期。一是上音的学生时代,一是1979-1981的中年时期,再就是2003年开始的晚期风格。那时,汪退休回到上海,新创作了《动物随想》、《读鲁迅“野草”》、《红土集》,根据以前的素材完成了《先知集》,改定了旧作《童心集》、《黑土——二人转的回忆》和《秦王饮酒》。2008年,汪因为身体的原因彻底搁笔。
2013年,汪立三在上海去世。

汪立三(来源:凤凰文化)
3
这几日,我反复听奕明弹奏的汪立三钢琴作品全集。奕明说汪是世界级的,我要好好进入。汪在学生时期的《小奏鸣曲》,已被苏联专家评价为“一个音也不能增加,一个音也不能减少。”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深知这份评价的分量,那就是准确性,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,是天赋加历练的结果。
汪自述少年时在青羊宫,一幅楹联印象极深。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;人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这段话影响了他一生,在艺术上体现为自然无碍,明晰清澈,这是很高的境界;生活中则万事不强求,随遇而安。这种人内心有坚定的尺度,视最高的美和想象力为终极价值,对自己的艺术语言充满敬畏,绝不哗众取宠,急于求成,所以汪总是修改他的作品,一直到病老搁笔。
汪立三现在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中国作曲家之一,另一个当然是江文也。汪完全具备现代主义审美意识,熟悉西方现代音乐的语言和技巧,但他的创作,是“为了表达他的内心世界,表达某种敲击他内心最深处的无以名状的东西”(孙慕天),因此没有刻意的求新与实验。他本能地处理理好了创新与永恒的关系,堪称大师手笔。“不管你手法新也好旧也罢,乐曲的紧张度(张力)、境界、布局构思啥的,这是古今中外都不会变的。”(奚其明)
汪立三很早就明确,要创作中国本土的音乐。他在香港“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”上的发言《新潮与老老根》(1986),视野广阔,思想深沉,在尊重传统与突破传统之间,就音乐的现代性,作了一番东方的想象。他从“单音内涵的丰富性”、“音体系的多样性”和“乐思发展的散文性”三个方面,论证了中国传统音乐,在形式和观念上,都有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的特征,在音乐美学上,有其独特的深度。而这些特征,恰恰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音乐,有很多的吻合。很显然,汪自己的创作,也是建立在对现代与传统的深刻反思上。在汪的音乐里,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素材,是怎样引导着他的精神游历,使他创作出了世界级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开放的,原创意义上的,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。
不知什么原因,汪留下的重要作品,全是钢琴独奏,没有管弦乐,也没有其他形式或体裁。这些作品,除了学生时期的《小奏鸣曲》,全部是标题音乐。这里有对民歌的改编,如《兰花花》;有对别的艺术形式的回应,如《东山魁夷画意》;有对古典诗歌的兴发,如《幻想曲两首—李李贺诗意》;有对个人生活和伤痛的记忆,如《黑土------二人转的回忆》。而汪自己最满意的《他山集》,五首曲目分别是“书法与琴韵”、“图案”、“泥土的歌”、“民间玩具”、“山寨”,则“熔铸着中国的传统文化,大地山河,人生与梦想。”事实上,我理想中的中国原创艺术,不论诗歌、绘画抑或音乐,都应该具有这种品质和深度。这才是汪立三让我着迷的原因。
汪的绝笔之作《动物随想》,奕明说表现了汪的被困与无法脱困,是他逐步失去记忆,要想起什么却又想不起来的写照。我听来却是另外一种味道。也许是有意无意的想象和误读,“大象的舞步”、“沙漠里的驼铃”、“归心似箭的燕子”、“玻璃缸里的珊瑚虫”、“困在笼中的大蟒”、“蜘蛛的八卦阵”以及“梦中的蝴蝶”这些题目,我看到的是自由,沉着,意有所属而不不黏人世,随心所欲而不逾矩。
汪立三的绘画和文学一直没丢,他后期甚至画抽象画,康定斯基那种路数,大笔触,强调色彩的表现力。他也喜欢给每个作品写上一首小诗。他的诗歌语言和意识,却是前现代主义的,那么,他的文学视野,想来应该到浪漫派为止。

江文也(来源:凤凰文化)
4
上个冬季的北京,常常重霾围困。一个早上醒来,窗外灰沉沉的,太阳发出惨淡的白光,像被装上了弱音器,百米之内的塔楼若隐若现,仿佛在炼狱中。我心有所动,写了一首小诗《霾中风景》:塔楼,树,弱音的太阳/构成一片霾中风景/鸟还在奋力飞着/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/记忆弯曲,长长的隧道后/故国有另一个早晨/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,我想/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。
这首诗写得很快,像是自然流淌出来的。写完后我突然觉得,在不经意间说出了内心隐秘的抱负。其实这些年来,我一直在循着这个意趣,像怀着一种乡愁,寻找堪为典范的前辈和同道。这一次,仿佛完成了一个命名,我觉得未来的工作,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。像汪立三一样,我也有着成都带来的慵懒和随意,因此对这个抱负的完成度,我并不是太在意。只是这个抱负本身,就让我喜悦,如博尔赫斯所说,时间的流逝会让我安心。
晚清以降,我们的文化就完全沉溺在对西方的想象中。我们已经忘记了,“美乃公器,天下共逐之。”其实,生命本身那种感觉,人类精神那种东西,有何进步可言。在一次访谈里,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:一个当代汉语诗人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,取决于他对传统的认识、了悟和转化能力。我相信这个价值判断,也可用在别的艺术领域。我发现江文也时,仿佛看到了一个新大陆。想想吧,他在1939年,就写出了《孔庙大晟乐章》,通过礼乐来召唤孔子的精神,“重建被剥夺的身份,恢复被割裂的传统”(王德威)。可惜时代错失了他,彼此都是悲剧。文学有个胡兰成,他的才情和语感,使他的写作有那么点意思了,精彩之处常让我扼腕:多好的汉语啊。惜乎这哥们志不在此,态度略略欠诚恳,文字就少了浩然之气。他本想做帝师,经天纬地,视文章为小技,最后还是文章为其留名。当代绘画,有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尚扬,他的《董其昌计划》系列,发展出一种具有“中国的、当代的、尚扬的”特点的强有力的风格和形式,“在有人类绘画以来,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中国还是美国,都无法找到对其定位的直接参照”(朱青生)。
一种文化的振兴,需要更多这样的托命者,汪立三也在这个序列列。他的很多思想和观念,应该成为中国当代音乐的重要遗产。除了前面提到的《新潮与老老根》,他还有一篇文章,《中国新音乐与汉语特点有关的若干理论与实践之回顾》(1990),探讨了汉语独特的语音语调,对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的影响。他写过一首艺术歌曲,歌词全用《韩非子》“滥竽充数”一节的原文。他先把原文读出来,再根据读音找音乐的音高。他甚至设想,将语音语调抽象化后,再把音乐中的其他参数代入,是不是能搞出新的作曲技法?而最让我吃惊的是,他提出了“超象思维”这个概念,认为在音乐创作中,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,都不起主导作用,起主导作用的是另一种思维,他称之为“超象思维”。几年前,我和夏可君力图为一种新的中国绘画命名时,有过多次探讨,中间曾提出过“超象绘画”一词,当然随后就否决了。冥冥中这种气息的相通,我油然升起一种会心的愉悦。
读《汪立三评传》,以及听汪立三也包括听江文也时,我有一个疑惑:似乎作曲家比诗人,在传统的现代转化中,更得心应手。奕明认为:“音乐上有一个便利条件,就是西方传统古典音乐那一套,在被20世纪的人解构之后,很多方面正好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观念。周文中等人就是在找这个结合点。葛甘孺是周文中的学生,也是这个路子。比如西方传统古典音乐讲究很准的音高,很准的拍子,音色方面,相信充分振动后的饱满圆润的声音是好的声音。后来这一切都被解构了。音高故意不准,而中国传统音乐就是讲究余音,绕梁梁三日,就是所谓音腔,就是在音高上的游移。拍子也被打散了,正好中国传统就有很多散板,古琴有,山歌(比如信天游)也有。音色被解构后,各种不充分振动的所谓噪音被引进了。可很多民乐器本来就是不充分振动的呀,比如琵琶,就是要听这种非常凄厉的金石之声。还有比如很多戏曲的唱法,秦腔啥的,就不是充分振动的声音。所以正好对接上了。”
这让我大受启发。虽然在“道”的层面,各类艺术是相通的,但毕竟载体或说媒介不一样。声音和色彩,是人类共用的语言,只需要在里面发现或制定新的方法和规则,就能出新的气象,建立新的风格。诗人就要焦虑得多。现代汉语几乎是一门崭新的语言,需要先被激活,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。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把握的过程,如同命运,要有特别的历史机遇,和一些强力天才的出现,才会结成正果。江文也和汪立三,都写出了成熟的音乐文本,打通了东西古今的关系,他们的诗歌,却只在一个很初级的水平。但江文也在音乐上的创造力,比如他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,先知一样,开出了一条路,确是一个典范般的存在。

汪立三(来源:凤凰文化)
5
行文至此,我问奕明,汪立三最吸引他的是什么。奕明微来短信:“一开始就是音乐本身。当时我大范围看了很多中国钢琴作品,他的作品很明显的跳出来了。当时接触的几部他的作品风格桀骜不驯,倔强,磅礴。不仅专业技术出色,而且一看就是有诉求有话要说的。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人的生平,仅仅是作品。后来了解更多生平,才知道音乐中这些紧张度大概是怎么来的。”此刻,我在大理理家中的花园里,苍山烟岚袅袅,云霓无尽,让人有往世之想。
作为一个钢琴家,奕明数年奔波,四处探访,做文字活,为汪立三立传。彼时,汪已到垂暮之年,除了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,基本上算是寂寂无名。因为这部评传,以及那三个多小时的钢琴作品全集,奕明把一个天才音乐家的形象和作品,完整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。这个世界,会因为留下了汪立三,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?比如,这会改写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史吗?我相信会的,汪立三是那种能改动历史秩序的音乐家,也就是说,大音乐家。
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弄潮儿,浮在面上。他们有着巨大的能量,总让自己处在某种中心,但对身处的文化,却没有一种有价值的态度,也谈不上任何回应。他们对当下生活,或一种时代精神,也缺乏深刻的感受。而真正自觉的创造者,大多只在一个“隐在谱系”(敬文东),在世时不为人知,他们也不在意,只做自己的事。这就需要有“二三素心人”(钱钟书),明白他们的价值,并传承下去。奕明就是这样的荒江野老,孤臣孽子,我理解他的苦心,敬佩他的工作。
大理的夏天,凉爽怡人,几乎每天都有雨水,洗得山峰碧绿,树木葱郁。我盛邀奕明过来,他首先问我家可有钢琴,我说我家没有,但潘洗尘家有。他遂告诉我,民国时代总共留存有一百四十多首钢琴曲,而他能够弹其中的四十多首,够开两次音乐会。他说他可以过来,为三五好友做两次沙龙,给真正的听众听,他也过瘾。我充满期待,但从这番话语,也觉出了他在繁华世界的寂寥。
我想我们都会同意,民国并不是一个时间,而是一种精神和气质,是林间吹过的悲风,池塘长出的青草,低空飞翔的燕子,是秦时明月,汉时空山。奕明对此情有独钟,由此开启他的精神计划,这是怎样的担当。他以一己之力,发掘出了汪立三,又和汪的亡灵,作了一场长长的对话,为这段历史,找回了一些坚固的记忆。身处一个价值日渐沦丧的浮世,我们能做的,就是忠于自己,像一株植物,只按本性生长,并不需要在乎风、鸟甚至人类的喜好。
现在,我要放下一切,去听奕明的汪立三,虽然这些天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。最好的创作,一定在语言上具备唯一性,只能感受和体会,用另外一种语言去描述它,是徒劳也是不智的。因此,我也无法用文字,来描述我听到的汪立三。我只想说,如果你进入了他的世界,那是一片锦绣图景,你对生活和命运的理理解,也许就会丰富一些。如果你要想进入他的世界,就只能去找张奕明弹奏的《汪立三钢琴作品全集》,NAXOS公司2015年发行。在此之前,你也可以先阅读这本《汪立三评传》。